流动视角下城市“周末爸爸”的父职实践研究
 AI智能总结
AI智能总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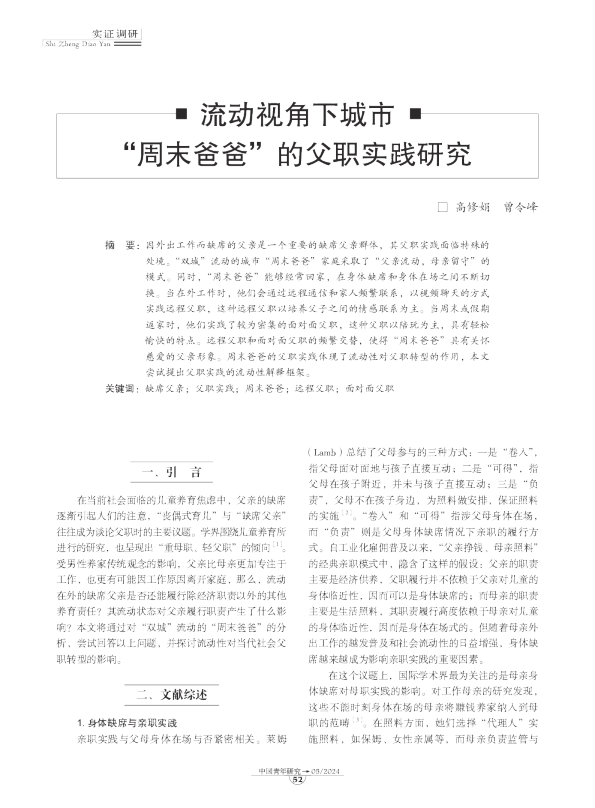
流动视角下城市 “周末爸爸”的父职实践研究 □高修娟曾令峰 摘要:因外出工作而缺席的父亲是一个重要的缺席父亲群体,其父职实践面临特殊的处境。“双城”流动的城市“周末爸爸”家庭采取了“父亲流动,母亲留守”的模式。同时,“周末爸爸”能够经常回家,在身体缺席和身体在场之间不断切换。当在外工作时,他们会通过远程通信和家人频繁联系,以视频聊天的方式实践远程父职,这种远程父职以培养父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为主。当周末或假期返家时,他们实践了较为密集的面对面父职,这种父职以陪玩为主,具有轻松愉快的特点。远程父职和面对面父职的频繁交替,使得“周末爸爸”具有关怀慈爱的父亲形象。周末爸爸的父职实践体现了流动性对父职转型的作用,本文尝试提出父职实践的流动性解释框架。 关键词:缺席父亲;父职实践;周末爸爸;远程父职;面对面父职 一、引言 在当前社会面临的儿童养育焦虑中,父亲的缺席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丧偶式育儿”与“缺席父亲”往往成为谈论父职时的主要议题。学界围绕儿童养育所进行的研究,也呈现出“重母职、轻父职”的倾向[1]。受男性养家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比母亲更加专注于工作,也更有可能因工作原因离开家庭,那么,流动在外的缺席父亲是否还能履行除经济职责以外的其他养育责任?其流动状态对父亲履行职责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将通过对“双城”流动的“周末爸爸”的分析,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并探讨流动性对当代社会父职转型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1.身体缺席与亲职实践 亲职实践与父母身体在场与否紧密相关。莱姆 (Lamb)总结了父母参与的三种方式:一是“卷入”,指父母面对面地与孩子直接互动;二是“可得”,指父母在孩子附近,并未与孩子直接互动;三是“负责”,父母不在孩子身边,为照料做安排,保证照料的实施[2]。“卷入”和“可得”指涉父母身体在场,而“负责”则是父母身体缺席情况下亲职的履行方式。自工业化雇佣普及以来,“父亲挣钱、母亲照料”的经典亲职模式中,隐含了这样的假设:父亲的职责主要是经济供养,父职履行并不依赖于父亲对儿童的身体临近性,因而可以是身体缺席的;而母亲的职责主要是生活照料,其职责履行高度依赖于母亲对儿童的身体临近性,因而是身体在场式的。但随着母亲外出工作的越发普及和社会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身体缺席越来越成为影响亲职实践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议题上,国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是母亲身体缺席对母职实践的影响。对工作母亲的研究发现,这些不能时刻身体在场的母亲将赚钱养家纳入到母职的范畴[3]。在照料方面,她们选择“代理人”实施照料,如保姆、女性亲属等,而母亲负责监管与 安排,发展出“代理母职”的实践方式[4]。对跨国母亲的研究则揭示了长期身体缺席对母职实践的影响。作为跨国移民工人的母亲往往长期身体缺席子女的生活,借助于高度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出“远程养育”的母职实践,即借助于电话、视频等廉价、及时的通信方式,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道德引导、学业指导、照料安排等[5]。通过远程通信,跨国母亲以一种“虚拟在场”的方式继续实践养育职责。对中国乡城流动的务工母亲而言,她们通过阶段式迁移的方式,交替实施远程母职和身体在场式的母职,“以协调子女/家庭照料和为子女/家庭发展提供经济资源”两者之间的需求[6]。可知,身体缺席改变了母职实践,“代理母职”和“远程母职”都在“负责”的层面上实现了母亲的参与,前者以“代理人”间接履职,后者则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达成母亲的“虚拟临近性”,继续发挥母亲的影响力,因此“远程母职”成为分析身体缺席时母职实践的重要内容。 父亲身体缺席对父职的影响则大为不同。工作时间中父亲的缺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会妨碍传统父亲职责的履行,工作本身就被视为父亲履行经济供养职责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兴起“参与型父亲”的话语,父亲的育儿参与和关怀气质都在逐渐增多[7]。研究表明,父亲育儿参与的增多并未减少父亲的工作时间,而更多是将育儿活动纳入父亲休闲时间的结果,因而父亲育儿参与更多体现在陪玩方面[8]。对于流动父亲而言,远程父职也成为重要的分析内容,只不过远程父职比远程母职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研究(尤其是早期的研究)指出,跨国流动会加强传统的父职[9][10][11]。跨国务工使父亲挣得更多收入,更好地完成挣钱养家的职责,但也使父亲远离家庭的日常生活,在与家人交流时倾向于展示权威性和纪律性,造成与子女的情感隔阂[12],或者逐渐被边缘化,变成“支票爸爸”[13]。近期的研究更多指向跨国父职的另一面,跨国父亲也可能通过远程通信,展示出更多关爱型的“新父亲”的特征[14][15][16][17]。如波泽(Poeze)对迁移到荷兰的加纳父亲的研究指出,这些父亲认同更加“卷入”的父亲理想,除了完成经济职责之外,他们还通过远程通信干预照料,努力培养父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在孩子的情感发展中保持一个活跃的角色[18]。李(Lee)则关注到韩国中产阶层的跨国父亲积极地调整了育儿活动的性别 界限,其父职实践展示了更多参与和关怀,父亲们更擅长表达感情[19]。对中国乡城流动的务工父亲而言,由于长时间不能回家,他们往往将物质和远程通信作为一种补偿,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子女的深厚感情[20],因此学者认为迁移增强了父亲的情感表达[21]。对另外一些因工作而流动的父亲而言,远程父职和在家父职不仅构成分析父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种父职之间的变动性,也是理解父职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22]。 总结而言,身体缺席对亲职实践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远程亲职也纳入亲职分析的范围,成为理解流动性家庭亲职实践的重要方面。 2.父职实践的流动性解释框架 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都关注到流动性家庭中亲职实践的新特点,这正是国际学术界“流动范式”兴起的表现之一。流动社会学发起人之一的厄里认为:社会学不仅要关注社会性流动,也要关注空间流动,去研究各种流动形态和偶发性秩序,而不限于静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23]。“流动范式”强调在关系空间中检视流动,在流动中检视社会关系,对社会互动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互动,也要关注由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的“想象性在场”的互动[24]。对于家庭领域而言,当代社会的家庭呈现鲜明的流动性,如“时空上的迁徙和变动,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家庭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已经不再是将家庭视为静态单位或理想模式的传统家庭研究视角可以理解的了[25]。吴重涵和戚务念在对留守儿童养育的研究中也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逻辑,使得学者们在研究留守儿童养育问题上,想当然地将物理空间上的隔离等同于心理、社会空间上的隔离,而忽视了不再共同居住的亲子关系得以维系的其他因素,如情感记忆、父母的不在场养育等[26]。因此,对于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流动性家庭,其家庭的基础不再是一个稳定静态的地理空间,而是由同处于不同空间的家人及其相互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和想象性在场的互动连接起来,其间的空间关系变动、信息流动以及家庭关系变动都会影响父职的实践。因此,本文尝试使用流动社会学的视角为流动性家庭中的父职实践构建一个解释框架。 首先,流动社会学批判传统社会学的“静止主义”——将有边界的、真实的地方定位为人类身份和经验的根本基础[27]。流动性的家庭已经不再以一 个固定的物理空间作为家的基础,而是“被手机提升了的父母”[28]。因此,在流动性解释框架中,身体缺席并不等同于养育职责的缺席,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父母仍旧能够履行父母职责。本文借鉴跨国亲职的相关研究,将远程亲职纳入分析的范畴,将流动父亲的父职实践分为身体缺席时的远程父职和身体在场时的面对面父职。同时,以两种父职实践都具备的“周末爸爸”群体的实证研究,弥补学术界此前更为关注长期身体缺席父亲的远程父职而忽视面对面父职研究的不足。 其次,流动视角需要把握变动性的社会活动的复杂模式[29],而不只是静态的类别。对于流动父亲而言,不只是需要描述两种父职实践方式,身体在场与身体缺席两种状态之间的变动性也至关重要。对于长期缺席的流动父亲而言,其远程父职是研究的重心,而对于频繁返家的流动父亲而言,缺席与在场的变动性也对父职实践产生了影响。此前,已经有学者分析了这种变动性,如奥雷(Aure)对挪威石油工人父亲父职的分析[30],肖索未和汤超萍对乡城务工母亲母职的分析[31],但这种变动性对中国流动父亲的父职实践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未有充分的描述与分析,本文将尝试在这一点上推进现有研究。 最后,流动社会学反对仅从结构性或者能动性分析社会现象[32],但也并非完全抛弃二者,而是可以将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融合起来。在流动父亲身上,其流动处境就含有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的结合,阶层、城乡、性别、文化、个体及家庭特征等诸多因素都影响其流动处境,也相应地影响了其具体的父职实践。因此本文的流动解释框架将在融合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的基础上,对流动父亲的父职实践予以解读,同时说明流动性对于当前中国父职转型所 起的作用。 基于以上诸种考虑,本文借助15位“双城”流动的“周末爸爸”的父职经验,探讨较为频繁回家的流动父亲群体如何履行父亲的养育职责,以及这种流动性的父职履行模式对中国社会父职转型又产生何种作用。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15位“周末爸爸”的故事,来说明城市流动家庭中父职实践的特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对象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在对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分析之后,对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回访,并访谈其中几位“周末爸爸”的妻子作为资料补充。本文目的在于了解特定流动状态下的父职实践行为,因而更关注他们的流动处境和父职实践方式的独特之处。研究中选择的被访对象具有以下共同之处:一是他们属于“双城流动”家庭,具有典型的“职住分离”特征,即父亲在一个城市工作,母亲和孩子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且这种“职住分离”状态持续一年以上。在城市的分布上,既有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周末爸爸”回家与孩子团聚的频率较高,每一周到三周回家一次。由于他们平时缺席,周末在家,因此用“周末爸爸”对这一群体进行命名。二是“周末爸爸”多数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多为脑力劳动者,如工程师、管理人员、销售总监、医生、建筑设计师等,年薪在20万元到50万元。三是年龄在29~40岁,家中有幼儿园或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或两个子女。15位“周末爸爸”的基本情况、流动状态及家庭育儿安排情况见表1。 表1城市“周末爸爸”个案基本情况 个案序号 父亲状况 子女状况(数量/性别年龄) 家庭状况 C01 38岁,�科,销售主管,工作在南昌,家在衡水,三周回家一次,在外四年,每周3~4次联络家人 2/男10岁;男8岁 妻子:大专,通讯公司后勤。爷爷奶奶同住帮忙照料 C02 29岁,大专,建筑设计师,工作在杭州,家在安庆,三周回家一次,在外三年多,约每天和家人联系1次 1/男3岁 妻子:大专,护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帮忙照料 C03 38,大专,销售经理,工作在沧州,家在衡水,一周回一次家,持续一年半,此前两月回一次家,约每天和家人联系1次 2/女14岁;男9岁 妻子:大专,职业培训。爷爷奶奶同住帮忙照料 (续表) 个案序号 父亲状况 子女状况(数量/性别年龄) 家庭状况 C04 34岁,�科,销售总监,工作在天津,家在济宁,经常出差,一周或两周回家一次,工作性质一直都是出差多,约每天和家人联系1次 1/女14岁 妻子:�科,小学老师。爷爷奶奶同住一个小区,帮忙照料 C05 40岁,硕士,汽车工程师,工作在上海,家在北京。原�一家人都在上海,为孩子上学考虑,妻子带孩子回北京,自己留在上海,每两周回一次家,持续3年,约每天和家人联系1次 1/女4岁 妻子:硕士,事业单位。外婆住在一起,帮忙照料孩子 C06 36岁,�科,国企管理人员,工作在合肥,家在芜湖,一周回一次家,外出一年半,约每天和家人联系1次 2/女7岁;男3岁 妻子:硕士,大学老师。正在读博,爷爷奶奶同住帮忙照料 C07 40岁,硕士,汽车工程师,工作在上海,家在北京。原�




